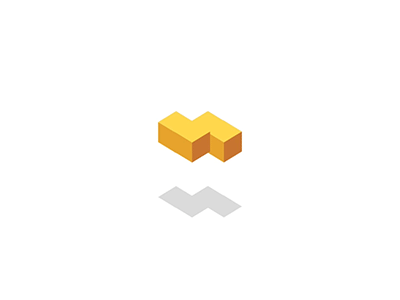父亲
陈敬容
太冷啊,冬之夜。
火盆里底火正熊熊地燃着,照红了围坐着的母亲,弟弟,和我底脸。我不住地把两手在火上晃来晃去,偶尔偷偷地望一望坐在桌前喝酒的父亲:他底脸,现在虽因几分酒意而带着点红色,不像往日那样冰冷地板着了,但我仍不敢多看,赶快又把眼光收回来,落在双手与炉火上了。
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,在这样的寒夜里显得多么寂寥呵。大家都沉默着;
母亲有时和父亲作一两句简单的问答,随后又复默然。厅堂里和楼板上,时有成群的老鼠跑来跑去,弄出很大的响声,惹得小猫咪呜咪呜地叫了:多难受呵,让人这样闷着!看一看弟弟,他也正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底脸;母亲呢,低了头不知在想些什么,只有她嘴唇动了一下,似乎要说话的,又咽下去了。
“什么呢,妈妈?”
“没有什么。”
无聊,来一个呵欠吧。但这个呵欠立刻传染了母亲,她接着也呵欠起来,疲乏地眨着眼睛。
“怎么,还早着呢。你们就瞌睡起来了?”
想是父亲听见我们呵欠,以为我们想藉故走开,因而发怒了吧?我们都胆怯地望着他,奇怪了,这回他脸上并无一点怒色,大家放了一半心。一是还早呢。
母亲有意无意地回答说。父亲看看我们,怪没意思摇摇头,使劲喝了一口酒;对着半朵摇摇欲坠的灯花,呆呆地不作一声。从那棕黑而带着倔强性的脸子上,不可掩饰地透露出十几年来奔走于军中的风尘。一个疑问不经意地飘进我底脑中:父亲怎么就显得有点老了呢,不是还不到四十岁吗?
但我马上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。我常常听人说,许就是父亲自已说的吧,说冬夜里一家老幼围炉坐谈,是一件最快乐不过的事。这时,不知有哆少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,正笑咪咪地坐在炉火之旁,听他们底父母讲—美丽的故事呢;一炉红红的炭火上煎着新茶,噜噜的沸水声伴着他们一串欢乐的笑,滚到炉火里,炉火是燃得更红了。
是吗,我不也正同着我底家人围坐在炉火边吗?
父亲要不在家,我们这时候也许正同母亲围炉笑谈,母亲谈着她底回忆中的童年,谈着一些好孩子的故事;有时也谈到我们底父亲,虽然我们并不要听。
也许母亲正躺在床上把小妹妹拍人甜蜜的小梦里去,弟弟正弄着劳作,或调配从《小朋友》杂志上看来的演魔术的药料,我则读着小说,或是手里捏了一管铅笔在练习绘画。冬之夜,永远是那样静静的,可是从未使我们有过寂寞感,父亲不在家,时光总是这样轻易地流了去,这中间,我们也用心念书,也好好游玩,在母亲底爱抚之下,如像深山的草木在阳光里,悄悄地,日继一日地成长。
母亲忽然呛呛地咳嗽起来,双手按着胸口,满脸胀得绯红。我连忙替她捶着背,弟弟走去舀了一杯热茶给她。怎么好呢,母亲身体近来越变越坏了,特别是几个月来父亲在家,事情多,她操劳过度,本来就不很强健的身体当然更容易遭病了。
我们常常怕母亲生病,但母亲偏常常病着。父亲不在家的时候,她病了我们可以陪她谈心,安慰她,有时我们底无知的话语不禁使她发笑。但是父亲在家了,每当我们日暮里放学归来,屋子里窗户紧紧闭着,窗纸上透着一层薄弱的黄昏的光,母亲床上的帐子沉沉地垂着,或是挂起一幅来,现出那用一只手支在枕上的惨淡的病脸;离床不多远,在一把大靠椅上坐着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人,那便是我们底父亲,口中正含着一只叶烟,两腿不停地左右摇动着,看见这种情形,我们只好慢吞吞地挨到母亲床边,问了一声好些没有,便把书包挂上,悄悄地畏缩缩地坐在一边,虽然心里有很多话想同母亲说,但一看到那张阴沉沉的脸,似乎正等着我们说错了或做错了一点什么,便好沉着声音来一个“妈的,”或竟致伸出那只有断掌的手;因此我们连坐着也不安起来,加以那闷气的房间,那窗上的薄薄的光……
而现在是放寒假的日子呢,要是母亲病倒在床上,叫我们怎样去消磨那从天亮以后的长长的时间呵。我一直望着她,希望看出她是健康的,是不会害病的;但是天呵,她那瘦瘦的脸,那陷进去的两个眼眶!我害怕而又不胜悲哀地俯下头去,用铁钳夹了一块炭放在火盆里。
父亲早喝过了酒,这时也走到炉边来,恰好坐在我和兹的中间。我们都不期然而然地向母亲身边挨拢一点。
“冰凡!”
教训来了,我想。
“你们什么时候开学?”
原来是这句话,刚才还听见他问过母亲的,现在怎么又问起我来呢?真奇怪!莫不是叫我下期别上学吧?我又疑惧着,因为我常常有这种危险的呵。不过一面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了他。
“那么到你们开学的时候,我已经不在家了呢。”
这话引不起我们一点兴趣,谁都不愿作声,于是散失到被炉火照红的空气中去了。一向除了骂人而外从不肯和我们多说话的父亲,今晚特别不同,好像一点寂寞都耐不住似的,又问弟弟:
“式行,你不是喜欢科学家的故事吗?我这回一定给你买一本《科学伟人传》回来,好不好?”
弟弟举起惊喜的眼睛向他望一望,回答了一个“好”字,就又低头默着了。
父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,也默不作声。炉火照见他紧锁双眉,眼望着一块块烧红的炭。
早就睡着了的小妹妹忽然在隔壁哭起来,母亲连忙站起,离开了这间温暖的屋子。当她跨过门限时,我想起几年间一个黄昏,为了点什么小事,父亲抓着她底胳膊,向门限那边一抛,把她抛得直挺挺地脸朝下面躺在地上,父亲还在这屋里骂着,摔着东西。我也记得,从那以后,健康的母亲就渐渐多病起来。
看着母亲一走,我和弟弟互相望了一眼,只想趁势也走开去,但刚要站起时又止住了,经验告诉我们,这样走了会被叫转来而且大骂一顿的,不如趁早别动吧。但是父亲却说了:
“过去帮帮你妈妈吧,我看你们也要睡觉了。”
于是我们立刻离开了火炉,离开了四面温暖的空气。跨过门限时我听到一声更长,更沉重的叹息。
母亲正轻轻地唱着,拍着小妹妹哄她睡觉,桌上一盏灯一闪一闪地抖动着;
我们一过来,便都很快地走到母亲跟前。
“今晚爸爸很想同你们说话的呵。”
母亲低低地对我们说,声音里带点唏嘘,我没有回答。
“可是说什么呀!”
弟弟抢着回答,一面用两手揉着眼皮。
这晚,当人们把一切喧哗都带到梦里去了,我悄悄地坐在灯下读一本什么小说(那是当父亲上街去了,我把零用钱托弟弟替我买的),隔壁有沉重的穿着布底鞋的脚步声在地板上拖来拖去,时而又停了下来,接着听得一声叹息。
窗外淅沥地下着阴寒的小雨,夜之森严充塞着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。
1935年9月于北平

点击图片可阅读《谈父亲》图书全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