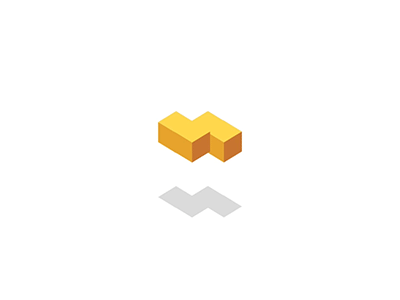所谓文学,都是给人以精神的享受,但弄文学的,却是最劳作的苦人,我之所以作诗作书作画,正如去公园里看景,产生于我文学写作的孤独寂寞,产生了就悬于墙上也供于我精神的生活。既是一种私活,我为我而作,其诗其书其画,就不同世人眼中的要求标准,而是我眼中的,心中的。
正基于此,很多年来,我就一直做这种工作;过一段,房子的四壁就悬挂一批;烦腻了,就顺手撕去重换一批;这种勇敢,大有"无知无畏"的气概。这种习性儿,也自惹我发笑,认为是文人的一种无聊。
无聊的举动,虽源于消遣,却也有没想到的许多好处。
诗人并不仅是做诗的人,我是极信奉这句话的。诗应该充溢着整个世界,无论从事任何事业,要取得成功,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;但心中永远保持着诗意,那将是最重要的一条。我试验于小说、散文的写作,回到生活中去,或点灯熬油笔耕于桌案,艰难的劳动常常会使人陷入疲倦;苦中寻乐的,只有这诗。诗可以使我得到休息和安怡,得到激动和发狂,使心中涌动着写不尽的东西,永远保持不竭的精力,永远感到工作的美丽。当这种诗意的东西使我膨胀起来,禁不住现于笔端的,就是我平日写下的诗了。当然这种诗完全是我为我而作,故一直未拿去发表。这如同一棵树,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,它就要生出叶子,叶子脱了,落降归根,再化作水、泥被树吸收,再发新叶;树开花,或许是为外界开的。所以它有炫目悦色之姿,叶完全是为自己树干生存而长,叶只有网的脉络和绿汁。
诗要流露出来,可以用分行的文学符号,当然也可以用不分行的线条的符号,这就是书,就是画。当我在乡间的山阴道上,看花开花落,观云聚云散,其小桥,流水,人家,其黑山,白月,昏鸦,诗的东西涌动,却意会而苦于无言语道出,我就把它画下来。当静坐房中,读一份家信,抚一节镇纸,思绪飞奔于童年往事,串缀于乡邻人物,诗的东西又涌动,却不能写出,又不能画出,久闷不已,我就书一幅字来。诗、书、画,是一个整体,但各自有不可替代的功能,它们可以使我将愁闷从身躯中一尽儿排泄而平和安宁,亦可以在我兴奋之时发酵似的使我张狂而饮酒般的大醉。
已经声明,我作诗作书作画并不是取悦于别人的欣赏,也就无须有什么别人所依定的格式,换一句话说,就是没有潜心钻研过世上名家的诗的格律、画的技法、书的讲究。所以,《艺术界》的编辑同志来我这里,瞧见墙上的诗书画想拿去刊登,我反复说明我的诗书画在别人眼里并不是诗书画,我是在造我心中的境,借其境抒我的意。无可奈何,又补写了这段更无聊的文字,以便解释企图得以笑纳。(文/贾平凹)